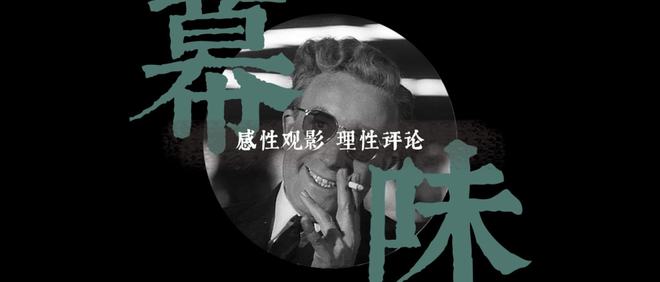
提醒:本文无剧透,可放心食用;有一点点哲学,不影响阅读。
《新蝙蝠侠》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焦躁。假如说生产力低下的传统社会人类的核心诉求是“我饿”,这么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的核心诉求很大程度上弄成了“我怕”。
蝙蝠侠之惩恶扬善同样利用焦虑的生产。也因而蝙蝠侠必须是时隐时现的都市传说,而不能深入人群。他必须与凡人保持距离以保持关于力量的神话。
而《新蝙蝠侠》里,蝙蝠侠在字面意义和精神意义都步入了人群,分享着作为现代人境遇意象的哥谭人的焦虑、焦虑和彷徨。
于是,他除了是挽救者,也必须在自我挽救。

在诺兰脍炙人口的三部曲里,蝙蝠侠身心极其强壮,正直、坚定、自信。他的强悍直接彰显在克里斯蒂安·贝尔那凶恶的体型和健硕的胸肌里。
虽然也有家庭不幸、爱人死亡和众人误会时的悲伤消沉,他的精神仍然强壮异常。强壮到第三部《黑暗勇士崛起》里他落到地牢时无钢索保护的“上升”(rise)都只变得理所应该。

而《新蝙蝠侠》里,蝙蝠侠是恐惧、迷惘和悲伤的。
这儿的蝙蝠侠既没丧失妻子,也没深陷千夫所指的窘境。他的滑翔技术还有待提升。下落时恶的力量虽然太过强悍,恶的生产虽然太过活跃,他的“正义”行动如同在海滩中将搁浅的小鱼儿掉进水里般无力,“能救一个是一个”……
直至先辈的一段不光彩历史被揭露,原罪的阴影旋即显得铺天盖地。在一些镜头里,脱下蝙蝠衣的罗伯特·帕丁森看上去有些矮小。更多时侯,蝙蝠面具遮不住眼中晶莹的眼泪。
笔者一度由于这个蝙蝠侠太“感伤”而有些嫌弃——这么多年了,嫩牛五方如何还在哭丧着脸哑着喉咙演惨白抑郁的青年?

但细想来,在诺兰三部曲那排山倒海的哲学思辨后,荧幕上出现一个这样的蝙蝠侠,也未尝不可。既不是重复,还略带意思:
让我们从诺兰说起。三部曲里最棒的是《黑暗勇士》。而《黑暗勇士》最美妙的地方是结尾。当蝙蝠侠为保留人们对正义和蔼的“信念”而弄成黑暗勇士绝尘而去的时侯,他浮现为《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描述的最正义者。
苏格拉底描述现实情景中的正义和不义:最正义者,背负着最不义的声名,曲折落魄;最不义者,顶着最正义的美名,快活一生。只有撕开哪个最正义者的皮,才发觉浮现出的虽然是僭主。
《理想国》里这一推演已然很具象了,文学作品中极少见那个作品能抽象化这一极端思想实验出的形象。但《黑暗勇士》以短短几小时几乎是炸裂般的重塑了这样的“最正义者”。
在那以后,《黑暗勇士崛起》里,成熟的英雄必须经历身陷险境之后再次精神升华这个环节。这一发展从继续推进人物形象的思路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但哲学思辨的力度相应就减小了。

而《新蝙蝠侠》里,不义主宰了世界,猖獗如斯,因而哥谭市无有所谓“最正义者”。
作为正义者的蝙蝠侠发觉了自身血液中飘荡的邪恶,发觉了自己作为装备的“恐惧”,更时常地被不义者借助,发觉了在都市的纸醉金迷中,人们不再嫉恶如仇,而是在焦虑中趋向僵硬。
蝙蝠侠的惩恶扬善虽说很酷,但一个身影一个符号远不能重建人们对秩序和正义的信念。
即便蝙蝠侠自己也处在那斯芬克斯之谜的叩问之中。灯谜人的谜团一步步将他引向一个旋转的黑洞,引向他自己信念的动摇和滑坡。

最令人绝倒的是——大反派灯谜人只是个戴着恶搞圆框墨镜说起话来一喘一喘的小职员,也不是爱德华·诺顿那样帅气的怯懦,而是生无可恋的迂腐。
想想帅得惨绝人寰的“小丑”和哈维·邓特,想想第三部里丑恶面具也难掩姿色的胸肌男汤老师,我得说,把大反派设置成一个各类意义上不起眼的小角色,是须要勇气的。
甚至,网飞的《小丑》里,华金·菲尼克斯出演的小丑仍旧穿着时尚,傲岸中自带矜贵。
而灯谜人——我甚至没散场时早已想不起他长哪些样子。他被“击败”后的哀求,倒是像我自己在各类失败后往往会发出的叫喊。

但这样单薄的反派,他对蝙蝠侠的挑战这么深刻。
蝙蝠侠尚且解开他的谜团。但面对他的蔑视,面对他“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一切,你也是我的一部份”的论断,蝙蝠侠难以回击,只得虚弱地用“精神病”(psychopath)来总结对方。
而我们都晓得,当辩论中出现“精神病”这样的功击时,意味着辩论的终结——确实,这世上有太多理智讨论难以讨论的恶。
这如同《老无所依》里哈维尔·巴登扮演的精典波波头杀手,你不晓得他为什么服务于恶,而恶却在这大地上猖獗成灾。

这么描画的勇气,一言以蔽之,是描画现实的勇气:现实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只是少数。
在“上帝死了”和“后真相”的时代里,大部份人甚至无需“贫贱”和“威武”,而是面对复杂的社会逐渐丧失灵魂,像被抽干了的便器般充溢腐朽的恶臭。我相信每位听众在听到“Nomorelies”的呐喊时,都多少会有共鸣。
这也正是灯谜的意义——我们必须依靠灯谜的诠释学步入深藏在我们内心的焦虑,发觉我们自身的症结,那也是击败焦虑和重建信念的第一步。
于是结尾处那一场暴雨的意义不言自明。那甚至不是意象,而就是《圣经·创世纪》中的开启了我们如今世界的暴雨——这个世界糟糕透了,救赎已无希望。必须彻底毁灭它,才可能在“白皑皑一片大地真干净”里迎来一个稍为不这么糟的世界。总之也不会更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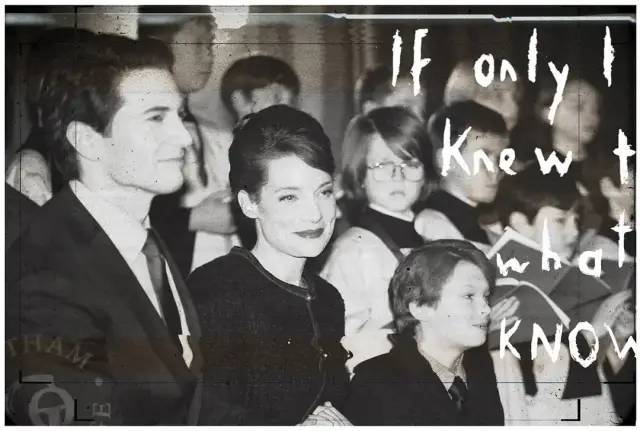
不过《新蝙蝠侠》的洪灾没有一个保留人类最后火种的正义者,也没有诺兰三部曲里蝙蝠侠炸了自己挽救哥谭人民的个人英雄主义诠释机会。而是人们手拉着手相互救治。
这个叙事其实很肉麻。
非常是蝙蝠侠在狼籍和黑暗中抬起火把的那一刻,我差点笑出声来——你很难想像中式个人主义超级英雄影片的晚会式的集体叙事化,但这儿它奇妙地发生了。

但这个微妙的转变何尝不深深反映了COVID-19时代人类的窘境——病毒像《群鸟》里孤零零的鸟雀般把人类赶进自己的钢筋水泥看守所,在隔离中人们透过窗子向外张望。
死亡、灾难和隔绝促使人们在精神上团结上去。共同的外伤催生了共同的愿景。人们从来没有这么渴求人与人的数学接触。
被无数哲学家思索过的与现代社会相随而生的“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趋势显漏出困窘。生产力落后时代生存需求促使的“在一起”(togetherness)的价值回归了。

在好多意义上说,《新蝙蝠侠》是老套的。老套的剧情推动(在视听媒介里,字谜创造的悬念是有限的),老套的音乐(好多动作戏的配乐一响我就手动跟唱《帝国进行曲》……),老套的爱情戏(我可以笑看蝙蝠侠“失身”大反派(如《黑暗勇士崛起》),但不是很能接受蝙蝠侠脆弱地求亲亲,亲了又亲),老套的结尾升华(重伤的男孩紧紧捉住蝙蝠侠不放手的那一刻,我似乎在看“感动日本”颁奖礼)……
甚至看蝙蝠侠和猫女挥别而后同行的那一段,我不由怨念:妈耶,诺兰的蝙蝠侠说甩锅就甩锅,“轰”得一声,一骑绝尘,猝然而止;这里如何“轰”了好几声还在“缠痴缠绵到天涯”……
在我看来,既然在蝙蝠侠的内核上早已做了跳出超级英雄和个人主义叙事的挑战,在视听上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么屈从于类型片而这么规整。

不过,在那之外,这样一个专属COVID-19时代的蝙蝠侠,确实可以供我们投射我们当下的喜(假如还有的话)与悲,焦虑与肿胀,恐惧与深切。
于是,面具之下,罗伯特·帕丁森那双一直饱含眼泪的耳朵,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疫情和经济危机后满眼疮痍的世界在哭泣。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信息真伪需自行辨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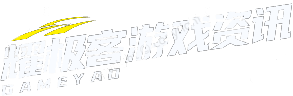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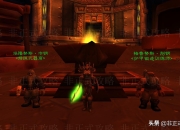




发表评论